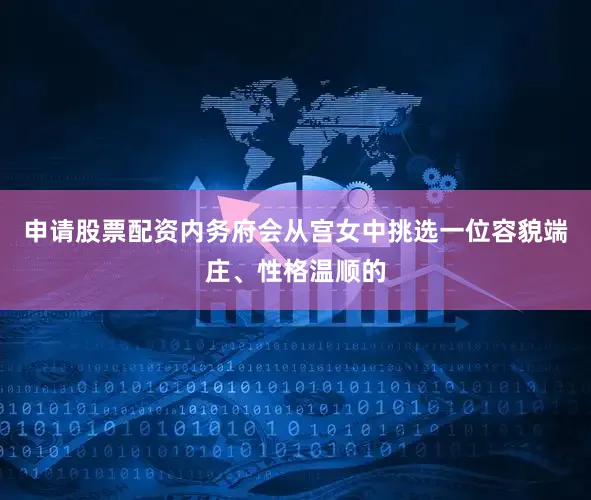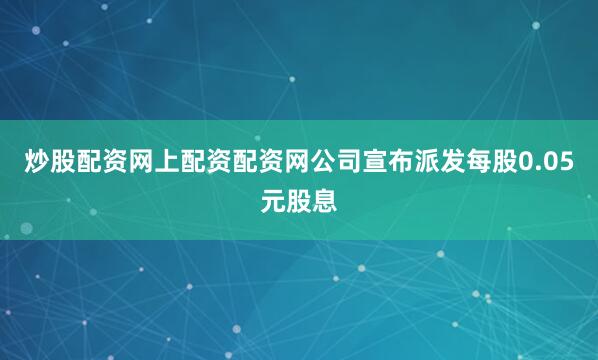
长光辰芯的招股书披露了一组微妙数据:2022年至2024年,公司营收从6.04亿元微增至6.73亿元,年均增速仅5.6%,但净利润却从亏损8410万元飙升至盈利1.97亿元。
扭亏的“魔术”背后,是2022年一次性计提3.65亿元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大幅缩表,以及行政开支从68.1%压缩至9.6%的成本手术。
而支撑营收的主力产品——面阵传感器,平均售价从2022年的4467元/片暴跌至2024年的2014元/片,价格腰斩55%。

毛利率的坍塌更为触目惊心。
高性能CMOS图像传感器的毛利率从78.2%降至65.3%,定制服务毛利率从50.3%缩水至39.1%,三年整体毛利率下滑17.2个百分点。
公司解释为“产业链成本波动”,但招股书同时披露:2024年向关联方客户A销售产品的毛利率高达94.43%,而同期非关联客户毛利率仅65%左右。
客户A的身份成谜,仅在问询回复中模糊标注为“境外采购大户转型关联方”,且2020至2022年对其销售额从3506万元暴增至1.36亿元,占营收比例膨胀至22.58%。
研发投入的“纸面繁荣”同样耐人寻味。
2022年至2024年,研发费用从0.84亿元增至1.30亿元,但研发费用率却从13.9%到21.7%再回落至19.3%,波动剧烈。
更矛盾的是,研发团队201人占员工总数50.1%,但公司全球注册专利数从2022年的2650项减少至2024年的2050项,技术产出不增反降。
科创板问询曾揭露:应用研发部“负责与客户沟通”,部分工作与技术创新关联存疑。

实控人王欣洋、张艳霞夫妇的资本操作堪称精准。
2025年6月IPO递表前,公司宣布派发每股0.05元股息,合计1850万元,而夫妇二人通过直接及间接持股控制公司49.53%股权,近半分红落入自家账户。
这并非首次套现:2020年至2021年,公司合计现金分红3687.5万元,但2022年亏损8410万元,引发监管质疑“是否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”。
耐人寻味的是,张艳霞持有瓦努阿图共和国永久居留权,这个2020年才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除名的南太平洋岛国,以低税率和宽松资金管制著称。
关联交易网络进一步编织利益链条。
供应商E同时是公司客户,长光辰芯向其采购外包封装服务,又以分销模式向其销售传感器;客户集团H既采购公司产品,又向其出售图像采集卡设备。
这种循环交易被交易所质问“是否存在业绩泡沫”,公司仅以“产业链协同”轻描淡写带过。
供应链风险被刻意弱化。
作为Fabless模式企业,长光辰芯将晶圆制造外包给Tower、DB HiTek等代工厂,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高达63.7%。
原材料中,硅片、引线框架等成本占比近40%,而国产硅片价格持续上涨;进口玻璃粉、硼源等材料因保质期短、运输周期长,存货减值拨备从2022年的1450万元增至2024年的3280万元。

科创板的失败经历暴露更多疑点。
2023年申报时,长光辰芯向股东奥普光电报送的净利润数据为-2401万元,但奥普光电公开披露的同期数据为-7900万元,差额达5499万元;凌云光披露的公司2021年净利润也与长光辰芯原始报表相差107万元。
交易所连发23问,直指“多套账目”“股东出资合理性”,例如凌云光曾以40万元货币资金置换估值100亿的无形资产。
估值暴涨的合理性同样成谜。
2021年股权激励时公司估值仅26.12亿元,但2022年6月外部股东入股估值飙升至100亿元,一年内暴涨283%。
高瓴、中芯聚源等近20家机构入场后,公司却于2023年撤回科创板申请,转道港股。
此次募资用途中,“补充流动资金”占比22.5%,与科创板撤回前规划的15.57亿元募资结构高度雷同。

客户结构的变化暗藏隐忧。
工业成像收入占比从2022年的49.5%猛增至2024年的66.3%,但主要依赖海康机器人、鑫图光电等头部客户,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仍达33.5%。
科学成像收入却从47.5%萎缩至28.6%,高端产品线增长乏力。
海外收入占比从33.9%降至26.0%,日本子公司对索尼的挑战成效未显。
员工持股平台的设计被质疑利益输送。
王欣洋通过杭州祺芯(个人全资公司)控制珠海云辰、珠海旭辰等5家员工持股平台,普通合伙人(GP)权益均由王欣洋独占,有限合伙人(LP)包括外部顾问。
这种架构下,持股平台产生的收益大部分流向实控人,而非核心研发团队。
医疗器械领域的布局尚未形成支撑。
2025年初发布的医用内窥镜传感器GXS1508被列为技术亮点,但招股书显示,医疗成像收入2024年仅占3.0%,不足工业成像收入的1/20。
子公司杭州辰芯、大连辰芯、长光圆芯连续三年亏损,封装产能仍处于试生产阶段。
国汇策略-哪个证券公司好一点-配资排行-哪个平台可以买股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